于这纷繁扰攘的人世,我们总在追寻一种生命的姿态,是深是浅,是清是浊,似乎永无定论。然而,当我默诵南朝诗人谢灵运“苹蓱泛沈深,菰蒲冒清浅”的幽渺之句,或是低吟北宋王安石“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的明丽之诗时,心头便悄然浮起一片光景——那是一种不尚深沉、不慕浓烈的生存意境,我称之为“清浅人生”。
何谓“清浅”?它并非浅薄,如浮光掠影般无所依托;亦非寡淡,如白水无波般失却真味。它是一种心境的澄明与生活的舒展,是滤尽喧嚣与伪饰后,生命本真的从容显现。英国哲人塞亚·伯林曾不无狡黠地说道:“我的愉快来自浅薄,人们不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此言初闻似谦,细品实傲。这“表层”,非指思想的贫瘠,而是对生命重负的一种自觉超脱,是对“静若安好”境界的悠然栖居。静与动,清与浊,深与浅,确乎是人生难以绕行的命题。世故练达的“老江湖”,其手段或可翻云覆雨,运筹帷幄,其智慧令人叹服,却总不免使人敬而远之;而那等直来直往的性情中人,虽或失之疏阔,却因其肝胆相照,不藏不掖,反更易令人心生亲近之喜。其中的区别,正在于“清浅”与“浑深”之间。
于是,我愿将“清”奉为心境的圭臬,将“浅”立为生活的航标。试观我们所寄寓的这个世界:地球表层,是生机盎然的绿与浩瀚无垠的蓝;太阳表层,是温暖热烈的丹红;而人的表层,最可贵的,莫过于那份不假雕饰的直率。这表层的色彩,正是宇宙为人类谱写的最本真的生命语言。做人不必追求那不可测的深渊、那灼人的内核,只需做到:任凭年华如流水般奔涌向前,在岁月的江面上,我只愿轻泛微波,不起狂澜。待到千帆过尽,风轻云淡之日,蓦然回首,那一片初心所映照的,依旧是清浅如昔的澄澈光景。这般人生,何其轻松,何其惬意!
你或许要问,在这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尘世,清浅如何可能?它难道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吗?我想,清浅并非要求我们全然摒弃智虑,退回蒙昧,而是要在心灵的深处,葆有一方不被流俗污染的源头活水。这“清”,是思想的明澈,如秋水之不染尘;这“浅”,是态度的率真,如童言之无忌。它需要我们时常涤荡心尘,勇于剥落那些为迎合世俗而披上的厚重铠甲,让真实的自我得以呼吸。当我们能以清浅之眼观物,便会发现,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但那份素朴之美,却愈发惊心动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境何深?其情何远?然而其笔下流淌的,正是这清浅自然的生命情调。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中蕴藏的禅机与理趣,又何其深邃,然其表达,又何其浅白从容。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简简单单的二十个字,更是把清浅自然景观和规律推向了极致。
其实,生命的厚重,未必需要以艰深晦涩的形式来呈现。庄子的哲学,汪洋恣肆,穷究宇宙人生之妙,却常借鲲鹏、斥鷃、庖丁解牛等寻常意象出之,其文可谓“清浅”之典范。弘一法师晚年,将佛家的圆融智慧,化入“咸有咸味,淡有淡味”的日常开示中,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这平淡,正是至深的清浅。反观当下,信息如潮,欲望如海,人们习惯于在社交媒体上经营精心修饰的形象,在人际交往中揣摩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将生活演绎成一场永不落幕的戏剧。在这层层包裹之下,那个真实的“我”早已疲惫不堪,面目全非,我已不我了。清浅人生,便是对这“掩饰式生存”的断然拒绝。它呼吁我们,勇敢地卸下妆容,坦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在简单与真实中,寻回那份久违的安宁与力量。
你简单了,世界也就简单了。这并非一句空泛的话,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核心的处世智慧。当我们的内心不再被过多的欲念和算计所缠绕,外在的纷繁与冲突,便也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根基。世界本是由简入繁,而智慧,则是化繁为简。我真诚地希冀,这世界能由更多的简单构成。而“清浅”,正是通往这种“简单”的绝佳尺度与标准。它是一种本真的、纯粹的、近乎透明的生命表达,它让存在本身,成为一首可以直接吟咏的诗。
故而,我愿追随这清浅的指引。在清晨的微光中,静静品啜一盏清茶,感受那源于草木的芬芳在唇齿间浅淡地化开;在午后的林荫下,漫无目的地散步,聆听风过树梢那清越又浅近的絮语;在夜晚的灯影里,与二三知己,说些清平浅易的真心话。不为深刻而故作高深,不为丰富而堆砌浮华。任时光的江水缓缓流淌,我只愿做那江面上的一叶轻舟,载着满船的星辉与月光,在清浅的波光里,从容地,驶向生命的远方。
待到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回望来时路,但见水波不兴,烟霞淡荡,心中唯有一片清浅的安然。南柯一梦,原来,与生命温柔相待,其密钥,正在这“清浅”二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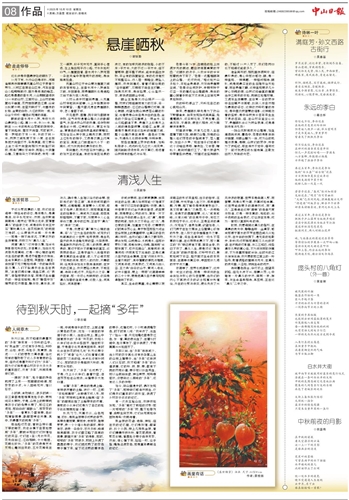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