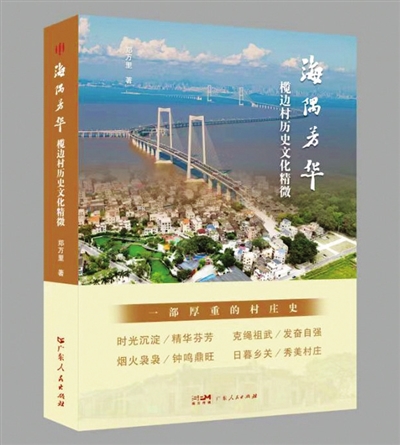忝为香山文化研究会员后,收到不少撰写评论的邀约,譬如郑万里《海隅芳华》(全称《海隅芳华:榄边村历史文化精微》)这本新书,盛情难却,我准备“戙起床板,彻夜奋战”,转念一想,人力不及AI力,不如让时髦的DeepSeek为我所用。果不其然,不消半分钟,一篇洋洋洒洒的书评呈现眼前。
DeepSeek抛出一个时尚而有深度的题目“一部微观历史的文化志”,我不禁眼前一亮,起首一段写道:“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版图上,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郑万里先生的《海隅芳华:榄边村历史文化精微》以广东省中山市榄边村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乡村文化志。”妙!我正在击赏之际,下面的话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从地理环境、建制沿革、宗族发展、民俗风情、建筑特色、名人轶事、方言特色和当代转型等角度,对榄边村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我可是刚读完此书,书中内容分为五章,加上前言、后语亦不过七章,何来八章?再仔细看看AI评论,不外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路,与书中内容形成“两张皮”。我在沮丧之余,觉得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了呼吸,都有着独特的灵魂。
“微观历史”的确是此书一大特色,但是,这里的“微观”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从细微处观照乡村文化,而是将宏观历史编织入微观叙述之中,又或者说,微观是一块投湖石头所引起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向宏观历史扩展。郑万里在第五章结尾点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写作缘由:“我始终认为,村庄是社会组织中最有生命力的根基,也是国家行政体制中最有生命力的根基。在传统观念里,村庄就是家,家的聚合就是国,家是经济基础,国是上层建筑。村庄稳,国就稳;村庄富,国就富。小河有水大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村庄与国家命运与共,国家与村庄生死相契,谁也离不开谁。村庄的昌盛,国家的兴旺,全都仰仗着生生不息的子孙们,任何时代都不能背弃他们,因为,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在。”
作者如何将微观与宏观勾连起来?他在每一章以某一两个人物为主线,通过接龙的写作方式,将历史名人一个个导引出来,最终编织出一幅星河灿烂的历史图案。榄边村是村民委员会,下辖赤坎、茶东、茶西、南塘、莆山、西江里6个自然村。该书第一章以赤坎村的阮章,第二章以茶东村的陈树棠、陈公哲、陈志昆,第三章以南塘村简让之、简崇光、简永照、简振兴,第四章以莆山村的陈吉润,第五章以西江里的林喜智为引线,写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史,写出海外华侨的奋斗史,写出榄边人为中国近代史殚心竭力的爱国史。这样的写作,看似写乡村,其实是在写一部中国近代史。
此书能让人一开卷便欲罢不能,大呼过瘾,郑万里的秘诀不是街头卖药的吆喝,一副膏药即时包治百病,而在于功力深沉,厚积薄发。
首先,郑万里文笔极佳。他写祠堂,“在国人心目中,祠堂不是一座简单的历史建筑,它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圣殿和精神家园,无论你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你的灵与肉都维系在那里。它刻录着你的生命密码,延续着你的血脉亲缘,提供着你所需要的巨大能量。”这些文字不虚浮,有深度,真让人击节,非浸淫文字工作数十载而不能为也。
其次,郑万里善于讲故事的同时,不时设置谜语,让读者一探究竟。如在引言部分,他竟然大谈特谈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不时谈赵子龙的故乡河北,我不禁疑惑这是写榄边村吗?直到后记,作者才揭晓谜底,“我的故乡在河北……当我了解到翠亨村靠山面海,走出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时,即刻就联想到我家乡同样靠北山面渤海,也曾走出中共创建者李大钊;当我得知左步村的先贤走南闯北,为家国而拼搏时,马上就想到了我的父辈闯关东上黑河的情景。此刻,我似乎明白了,文学上的缘分应该是两个同质的原乡信息源恰如其时地偶遇,进而产生同频共振的感觉与默契。”郑万里不仅仅写广东南朗的乡村,而是在写他自己,写他的乡愁。
其三,郑万里将现实与想象、史料与细节熔冶一炉,填补读者心中空白。这一切得以实现,纯属归功于作者的文学功力。书中第一章写中共四大代表之一的阮章,郑万里从史料和实地调查中钩沉阮章的生平,进而浓墨重彩地描绘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史。他写阮章的细节,重点放在一件在上海永安百货购买的呢绒大氅。永安百货是香山人开设的,故与阮章有着接龙式的联系。
话题回到永安百货。
阮章在永安百货转来转去,终于在四楼找到了男士衣帽柜台,那里的衣服琳琅满目,款式繁多。一个服务生走过来热情问他有何需要。
他客气地说:“想买一件大氅。”
服务生指着一件深蓝色呢绒毛领大氅说:“这是刚上市的皮毛大翻领外衣,卖得很火。”
阮章一直盯着这件大氅,看得出,他很喜欢,只是价格有点贵。他问服务生能否便宜点,服务生告诉阮章:“永安的商品不二价。”
李逸看出了阮章在犹豫,忙说:“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喜欢就买吧,做个纪念。
历史是沉默的,在郑万里笔下却是鲜活有声的。阮章的大氅是否在永安百货购买的,他是否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对话?这些细节在历史学家眼里满是疑问,郑万里却给我们带来美好而肯定的答案。
《海隅芳华》的阅读无疑是令人愉悦的,但“一部厚重的村庄史”该如何书写,却是一具绕不过去的问题。郑万里不像人类学家一样描述村庄的土地、人口、制度等主题,而是以新闻采访的视角书写与村庄有联系的人物,似乎与其副标题所言的“历史文化精微”相符,是一种大写意的书写方式,而不在于工笔描绘。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书中所写的人物与榄边村有多大干系?除了陈树棠、林喜智、陈吉润几个人物出生在榄边村之外,大多数人物是在外地出生和成长的,榄边村只是他们履历中的籍贯而已。阮章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唐山,读书在天津;“陈公哲,中山南朗茶东村人,1890年出生于上海”;陈志昆是孙科的英文秘书,是孙科夫人陈淑英叔叔的儿子,出生于夏威夷;“简瑞超于1921年7月25日出生于唐山”。并且,书中人物具有共同点:离开故土,外出打拼天下。那些在榄边村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大多数民众只是沉默的背景。
郑万里写过的阮玲玉真的是香山(中山)人吗?胡波的《阮玲玉评传》被列入“香山文脉丛书”,而阮玲玉除了籍贯是中山之外,乃不折不扣的上海人。如果从空间的生产角度而言,上海的空间才能诞生阮玲玉这般角色,中山的空间只为阮玲玉的DNA生产贡献力量。籍贯成为地方文化归属的纽带。如果我们是铁面无情的判官,大可判决籍贯标准无效,那么涉及地方文化研究的利益链面临崩溃。若我们从正面维护籍贯标准的合理性,乡愁是个不错的回答。郑万里在引言中指出,祠堂代表着“根祖文化”“延续着你的血脉亲缘”“这是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不管你生在哪里,长在哪里,抑或死在哪里,血液里的东西永远磨灭不掉,中华文化的韧性就体现在这里。”祖先崇拜是乡愁的基石,“游子的乡愁是伴随一生的,直到终老仍然盼望着魂归故里。”
为什么书中所写的都是一些远离故土、扬名在外的人物?郑万里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恰好与香山的村庄有着内在联系。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里安土重迁,营生往往相同,形成了如百足虫一样机械团结,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写照。而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兴起,西风东渐,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香山村落已逐渐被纳入这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时空开始重组,务农的榄边村人,怀揣着致富梦,走向上海,走向唐山,走向夏威夷,走向美国旧金山,他们虽然与世界其他部分形成了有机团结,却念念不忘故土,即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远的世代,生生不息的是由血脉铸成的乡愁。由此可见,地方文化由两个阶段构成,一个阶段是“输出”,榄边人走向世界,建功立业;另一个阶段是“反哺”;榄边人或其后代,从世界走向榄边村。榄边村与世界,微观与宏观,终于握手言和,在郑万里的《海隅芳华》书中。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