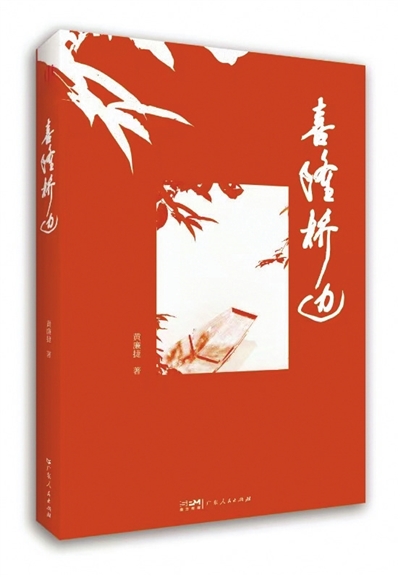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将“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深度贯通,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山实践,助力中山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市,推动香山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走出大湾区,走向全世界,即日起,中山日报与中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开设“艺评”版,以文艺评论为纽带,聚焦本土文化,挖掘表达时代精神。
欢迎广大读者投稿,投稿电子邮箱:2469239598@qq.com,欢迎短评(1500字以内)。
《喜隆桥边》作为黄廉捷深耕乡村题材的文学实践,其现实意义并非简单的时代镜像所能涵盖,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乡村变革的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复杂的光谱。当时代急流冲刷着乡土根基,发展与坚守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在相互拉扯中形成微妙的张力场。发展从来不是对乡土的全然消解,坚守也绝非故步自封的执念,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往往会催生新的表达形态。
《喜隆桥边》的精彩亦在于此,正是这种多重书写,才让我们看到了辩证背后的人性光晕。在变革的洪流里,每个乡土个体既是被时代裹挟的尘埃,又是重塑乡土形态的力量,他们的奋斗与抉择恰好构成乡村变革最生动的画卷。
一
从题材的现实观照角度讲,《喜隆桥边》聚焦返乡青年创业,看似呼应了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当我们追问“何为真正的振兴”时,思辨的空间便随之展开。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小说中陈大阳、黎秀芬等知识青年带回的“新观念与新技术”,究竟是对乡土逻辑的充实,还是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变革,这让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的伟大论断。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亦在于先农村后城市,中国的伟大复兴同样有赖于农村的复兴。在当代语境下,“农民问题”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涉及主体性的重新定义。当知识青年以“改造者”姿态介入乡村时,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乡土社会中“人情大于一切”的隐性规则?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中“人才作用”的发挥,究竟是科技力量的单向输入,还是新旧力量相互驯化的结果?这些问题的悬置,让作品对“人才与乡村”关系的呈现,既具有时代共鸣,又留下了值得深挖的张力。
小说中的喜隆村是广府人、客家人与潮汕人共处的村落,堪称乡土中国文化生态的微缩样本。表面是“文化差异引发冲突”的线性叙事,实则暗藏着更复杂的文化博弈逻辑。多文化交融地带,往往是文学叙事的富矿。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奈保尔成长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里是多元文化交织的典型场域,印度裔身份、英国殖民影响、非洲与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碰撞,构成了他笔下世界的核心张力。多元文化的浸淫,使他的作品天然带有对周围环境的敏锐洞察。《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印度移民在殖民语境下对“家”的徒劳建构,是文化根脉与现实土壤游离的隐喻;《大河湾》里,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间的摇摆,展现了文化交融背后的博弈。他以冷峻笔触剖开的恰是多元文化相遇时,既和谐共生又各美其美的文化图景。这种对“交融”本质的深刻解构,与《喜隆桥边》乡土社会的文化博弈形成跨地域呼应,只是前者更多带着殖民后遗症的荒诞与疏离,后者则藏着乡土中国在转型中的温度与韧性。陈大阳与黎秀芬的爱情离合被置于家庭纠葛的框架下,若仅将其归因于“文化观念差异”,或许简化了现实的肌理,文化冲突的背后,是否还交织着资源分配的博弈、宗族势力的消长?更进一步说,“文化融合”的理想状态究竟是“求同存异”的温和妥协,还是“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当作品展现村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时,其实也在追问: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是要锻造一种同质化的“新乡村文化”,还是要守护多元文化共生的生态?这种对“融合”本质的叩问,让文化叙事超越了表层的风情展示,触及了乡土文化现代转型的核心矛盾。
《喜隆桥边》创作手法的独特性,暗含着形式与内容的思辨。散文诗般的语言、清新俊逸的笔调,将农村创业的艰辛转化为“情感与场景交融”的诗意表达,这种叙事美学是值得玩味的。当乡村现实中的泥泞与挣扎被赋予抒情性,是让读者更易共情乡土之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消解农村发展的沉重感?青春化叙事语态对“新农民精神风貌”的呈现,显然拉近了与当代读者的距离,而“青春”的昂扬与“乡土”的厚重之间,则形成了一种叙事张力。当我们用年轻人的视角观察乡村时,会不自觉地过滤掉那些更复杂、更粗粝的历史沙砾。
作品的个性,恰恰构成了其思辨价值的延伸。对文化冲突的展现犹如“塘笼烟雨”,并非创作的优柔寡断,而是现实本身难以穷尽矛盾层级。当经济利益与文化认同缠绕在一起,当政策引导与民间自发形成角力,任何单一叙事都难以涵盖文化融合的全部真相。同样,对创业选择、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议题的“涉及至深”,也会引发读者的思考:乡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追求“全景式扫描”,还是“聚焦式深挖”?《喜隆桥边》选择以一个青年与一座城市、一位姑娘、一条鱼的主线叙事,这种叙事的取舍是对时代焦点的精准捕捉,它巧妙地规避了“高大全”式的糟糕叙事,从一个小切口进入,去窥探乡村世界的深层逻辑。
归根结底,《喜隆桥边》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乡村振兴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将那些悬而未决的命题抛给读者,当乡村在“现代化”标尺下被审视时,我们该如何定义“发展”的内涵?当多元文化在乡土场域中相遇时,“和谐共生”的边界在哪里?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追问,让作品在时代感与现实意义之外,增添了一层穿越表象、直抵本质的思辨重量。
二
《喜隆桥边》的“深描”尤为精彩。文学中的“深描”旨在对细节进行多层次富有暗示性的描写,它不仅呈现现象,更揭示其背后的意义与关联,它是作品的“因果链”。因为“深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像链条上的环节,既暗示前文的“因”,也推动后文的“果”,让故事情节和人物行为的逻辑更自然且深刻。以《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为例,“深描”的细节包括黛玉对落花“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执念、葬花时的呜咽、对“一朝春尽红颜老”的悲叹。这些“深描”的“因”藏在她的身世和对纯洁的坚守中;而它们的“果”则贯穿全书,既强化了她与宝玉“知己”的共鸣,也为她最终“泪尽而逝”的悲剧埋下伏笔,让她的结局因这些细节铺垫而显得顺理成章。再如《阿Q正传》中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深描”,当他被打时念叨“儿子打老子”、被嘲笑时自夸“先前阔”,这些细节不仅刻画了他的麻木,更暗示了其性格形成的“因”,即底层社会的压迫与精神扭曲;而这种性格的“果”,则是他在革命来临时的盲目跟风,最终被当作替罪羊处死,让个人悲剧与时代背景形成紧密的因果关联。可见,“深描”通过细节的“因果”串联,让作品的情节发展、人物命运都有了内在逻辑支撑,使故事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喜隆桥边》刮鱼场景的刻画堪称“深描”的优秀范例。它不只是对劳作过程的写实,更隐藏着乡土社会的权力密码与情感逻辑。鱼鳞飞溅的弧光里,或许有五叔对土地的敬畏与不舍;渔网收紧的力度中,可能暗含着陈大阳作为新一代农民与乡土传统的角力。这种描写让“鱼”超越了生物属性,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隐喻。正如鱼在水中的浮沉,乡土伦理也在新观念冲击下,经历着溶解与重构的阵痛。作者与人物“休戚与共”的姿态,让这种描写避免了旁观者的猎奇,转而成为一种沉浸式的共情。当刮鱼的“大网”划破水面的平静,也划亮了乡村振兴的黎明。
喜隆村作为广府、客家、潮汕文化的交汇点,其“深描”的价值更在于对文化融合悖论的揭示。多文化共生的表象下,是“融合”与“冲突”的永恒拉扯。或许一句方言的误用便触发宗族记忆的敏感神经,一次婚俗的妥协竟牵扯着资源分配的隐秘博弈。这让人想到奈保尔笔下移民群体的身份撕裂。不同的是,奈保尔以冷峻旁观揭示殖民后遗症的荒诞,而黄廉捷则在温情叙事中,触摸着文化碰撞的温度与重量。当广府的务实、客家的坚韧、潮汕的抱团在田间地头相遇,所谓“融合”从来都不是文化基因的简单重组,而是在利益与情感的反复博弈中,生长出新的乡土伦理。这种描写跳出了“文化多样性”的表层赞美,而是直抵“如何在差异中共生”的时代命题。
《喜隆桥边》对“中国乡土精神”的探勘,更显其思辨锋芒。它没有将乡村振兴简化为“青年创业成功”的线性叙事,而是在人物的情感波动中,挖掘大时代下个体的精神症候。陈大阳对城市的疏离与对土地的犹疑,黎秀芬在传统婚约与自由爱情间的挣扎,本质上都是转型期中国人“精神家园”失落与重建的缩影。这与南非作家戈迪默在种族隔离背景下对人性困境的书写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戈迪默以种族隔离为镜,照见人性的幽暗与光辉;黄廉捷则以乡村变革为窗,窥见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跋涉。因此,《喜隆桥边》“深描”的意义,不止于文学技法的创新,它通过对乡土细节的精准捕捉,让我们得以在鳞片鱼影的反光中看见文化的韧性,在青年的迷茫中触摸时代的脉搏。这种描写不提供标准答案,却以其思辨的深度,迫使我们直面那些关于根脉与未来、坚守与变革的永恒追问。而这,正是新时代乡村叙事最可珍贵的精神品格。
三
在文学创作中,方言写作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为作品赋予了别样生命力和地域文化色彩。《喜隆桥边》就是这样一部巧妙运用中山乡土语言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对本土方言的深度挖掘与运用,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语言层面构建起一个鲜活且真实的岭南水乡世界。
中山方言种类繁杂,广府话、闽南话、客家话在此广泛使用,“十里不同习,五里不同语”是其生动写照。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在表现,恰似水面涟漪映照水底暗流,我们既依赖它勾勒思维的轮廓,又无法复刻暗流的全部精彩。词语的确定性与思维的流动性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隙。然而,正是这道裂隙催生了思维的深化。当我们为一个模糊的想法搜寻最贴切的表达时,语言的逻辑会反过来梳理思维的脉络,迫使混沌的感知走向清晰。或许,语言从不是思维的完美镜像,而是思维的锻造炉。它既暴露着思维的边界,也在一次次“词不达意”的挣扎中,推动着思维拓展新的疆域。我们用语言叙述思维,最终却发现,思维也在被语言重塑着模样。可见,语言的丰富性反证着思维方式的丰富性。中山得天独厚的方言文化,是《喜隆桥边》搭建方言叙事的优渥土壤,它使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与故事铺陈充满浓郁的地方韵味,仿佛将读者带入沙田地区的大街小巷,目睹当地人的生活日常。如“无裤着”“衰佬”“刮塘”“阿五”“得食”等;再如“烧乳猪”“脆肉鲩”“妙龄乳鸽”“小榄鱼球”“沙溪扣肉”等,还有一个顺口溜很有乡土味:
日捱夜捱,砧板破晒。
家中无食,拼命来捱。
日做工,夜做工。
腰骨弯了,背脊烂晒。
破裤穿着,汗水流完。
耕田人仔,无日欢容。
这些带着露珠的乡土词汇,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元的中山方言,也丰富了小说语言的层次与内涵,使读者从语言层面感受到乡土文化的丰富性与交融性。
《喜隆桥边》运用中山乡土方言,不仅是简单的词汇罗列,更是将方言融入人物性格塑造与情节发展之中。不同方言区的人物,其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性格特点和文化背景。比如,来自不同方言区域的青年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因方言差异产生的小误会、小摩擦,不仅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还进一步深化了多文化交织下矛盾与融合的主题。这种对语言与人物、情节紧密结合的处理方式,让方言成为推动故事发展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有力工具。
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方言写作是对地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法国作家米斯特拉尔曾坚持使用几近灭绝的普罗旺斯语创作,最终拯救了弥漫着薰衣草香味的普罗旺斯文化,自己也因“他的作品犹如一座高大不朽的纪念碑,用以荣耀他所钟爱的普罗旺斯文化”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作家金宇澄的《繁花》,将上海话的节奏、语法、思维方式和韵味,巧妙地融入叙事之中,创作出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叙事奇效。广东老作家陈残云在《香飘四季》中,大量融入粤语农谚,如“春争日,夏争时”等,人物称呼如“阿嬷”(奶奶)、“细路哥”(小孩)等,这些词汇就像地理导图,起到读者对号入座的作用。《喜隆桥边》通过对中山乡土语言的运用,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岭南乡村文化的窗口,让那些并不十分活跃的方言词汇和独特表达方式,在小说中得以鲜活起来。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四
《喜隆桥边》作为一部适配移动端阅读的小长篇,其文本形态与精神内核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短视频时代文学创作的典型样本。它以“简洁流畅”的现代叙事为表,以“向下植根、向上通达”的精神纵深为里,在碎片化阅读的表层需求与文学性的深层追求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平衡的美学关系。
从文本肌理来看,“小长篇”的体量选择一定暗含着对媒介变革的回应。在移动端阅读场景中,注意力的碎片化与阅读时长的随机性,要求文本必须具备“驿站性”和“再进入性”,而《喜隆桥边》的“简洁流畅”恰好规避了传统长篇的繁复铺陈与多线缠绕,以生活化的线性叙事为骨架,让每个章节既构成相对完整的生活段落,又串联起整体的精神脉络。这种结构处理,看似是对短视频时代“短平快”阅读习惯的妥协,实则是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当文字剥离冗余的修辞外壳,反而更能凸显生活本身的质感,正如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对驴、风、树的书写,于极简中见丰饶,让寻常事物自然生长出隐喻的枝蔓。
更深层的价值还在于,作品将“生活化视角”转化为连接世俗与精神的桥梁。移动端阅读的受众群体,往往在日常琐碎中寻求情感共鸣与精神突围,而《喜隆桥边》对“平常人生存状态”的关切,恰如其分地切中了这种需求。它不依赖戏剧化的冲突制造看点,而是以近乎白描的笔触记录返乡青年的创业细节、多文化村落的日常互动,让鱼塘的波光、方言的顿挫、劳作的汗滴都成为可触摸的生活符号。这种“向下植根”的书写,与刘亮程对村庄事物的哲思形成跨越文本的呼应。刘亮程让驴成为时间的见证者、风成为命运的信使,《喜隆桥边》则让创业的艰辛、文化的碰撞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两者都在“寻常”中发掘“不寻常”,使生活化的叙事自然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追问。
更值得思辨的是,“适应移动端”绝非对文学深度的降维。短视频时代的阅读习惯,往往被诟病为消解思想的“杀手”,但《喜隆桥边》却以“向上通达”的精神高度,打破了这一偏见。它的“简洁”并非简单化,而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克制,在生活表象下埋藏精神暗线,即返乡青年对土地的犹疑,实则是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与重建;多文化的碰撞,隐喻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困境。这些精神命题并非通过直白的议论呈现,而是寄寓在鱼塘的经营、爱情的离合、琐碎的生活等场景中,如同水中的盐,无形却渗透肌理。这种处理方式,既适应了移动端读者“轻阅读”的心理预期,又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精神的浸润。当读者在碎片时间里触摸到这些生活细节时,便已在潜移默化中踏上通向精神高地的阶梯。
由此可见,《喜隆桥边》的媒介适应性,本质上是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重新定义。它证明,移动端阅读的兴起并非文学的终结,而是催生了新的表达范式:当文字从纸质载体的“神圣性”中解放出来,反而更能贴近生活的本真状态;当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文学的精神内核更需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存在。这种创作实践,与刘亮程的写作一脉相承,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真正的文学,既能在时代的媒介变革中找到扎根的土壤,又能始终保持向上生长的精神姿态,在世俗与神圣之间,搭建起永恒的桥梁。
(作者系中山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山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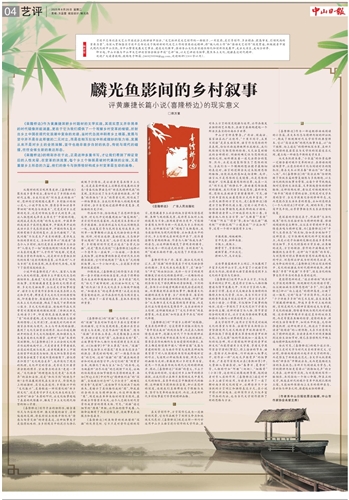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