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已然接近尾声,而寒意却久不散去。拖着病恹恹的身子,我颤抖着从校门走出。风,如锋利的刀刃,刮在脸上,一丝丝的痛。寒气肆意钻入袖口,冷得发麻。我急忙躲进母亲车里,可狂风的不羁,还在我耳边嘶号。
双眼紧闭,直到听见母亲喃喃自语:噢,木棉花开了。
抬起沉重的眼皮,我顺着窗外望去,远远的,如星星点点,深红几簇,随着汽车的前行而渐渐清晰。任凭狂风肆虐,他们仍不忘舞蹈,缕缕鲜红摇曳,毫不掩盖地展示他们的风采。常言梅花“凌寒独自开”,这木棉,却也总是开在这料峭春寒中。
来不及待我细细品味,一晃脑,它便扬长而去。
再一次闭上这困乏的双眼,往事慢慢飘到我眼前,我的思绪如扁舟一般,慢慢游荡;我又看到了那木棉,带着春意,开在校园门口前,她迎风招展,迎接着开春复学的莘莘学子,那是我的初中。暮春时节,棉絮纷飞,宛如一场鹅毛大雪,洋洋洒洒,在这南国,恰似一幅奇妙的风景。我吞了吞口水,仿佛又尝到那棉絮的苦涩。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暖烘烘的棉被便是由这些雪白之物所充斥,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深信不疑。对于木棉花最初的印象,应该是小学城南吧。校徽上的木棉,终是默默一直伴了我九年。
那时候的我会到滨江长廊捡起木棉花,拼出一个又一个的图案,我会待在一旁,静静地看别人玩耍。不过,若要说等我知道木棉花是市花为何时?我想,也已经是这9年中的最后一年了。
校徽上的木棉,无法再伴我三年,但我与木棉的邂逅,却从未停止。高中的校园很大,不知名的花草更多,一条名为“绿荫路”的小道,连接着两个校门。于我而言,我会在闲暇之余漫步此道,倚靠在略微发凉的石凳上,抚摸着那些代表历史的石刻,晨间有鸟鸣,黄昏有落叶,而路旁的木棉树干笔直得像肃立的战士。金山育英才,一代又一代。桃李遍布,又有谁能记起校园的蝉鸣,记起那泥土的芳香?“曲径通幽”,用来描述它再好不过。
汽车慢慢驶进乡村,老家的路悠长而有内涵,每每来到这里,心中莫名地安静了许多。琅琅的读书声从充满希望的学校中传来,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树影,屋檐下有鸟雀在搭巢,嬉闹声从操场上传来,孩子们的笑容微微荡漾,我趴在车窗前,静静地看着。车子终于停下,盼望着风景的我终于不顾寒风的震慑而急迫地走出。头上就是木棉,上端的花开得热烈,而在她们底下的,是待放的花苞,一颗颗的、一串串的、圆圆鼓鼓的、三五成群的,像极了葡萄架上的果实。抬头望去,便是一抹灿烂的深红,可她们不甘示弱,终有一天也能绽放自己的光彩。
我走进乡间的小道,田野中有一首首曲子,蓝天白云,不时传来几声鸟鸣,小贩的叫卖声,鸡狗的鸣叫声,补全了这和谐天地的最后几道乡音。随着流水般的乡音入耳,那矗立的木棉,带着我的思绪再度辗转。回过神时,也已经走到家门口。春风掠过眼角,带走了丝丝晶莹,里屋的家人,还在向我招手。回头望去,是屋外的木棉翩翩起舞。
以前,我埋怨春日,因她不告而别。如今我理解春日,因她自冬日便已显露痕迹。她不告而别,是怕你有太多眷恋,她藏在深处,早早就把你端详。我拨开心中的愁云,脚步也变得轻快,我微微一笑,沐浴冬日的暖阳。
城南有旧事,城南花已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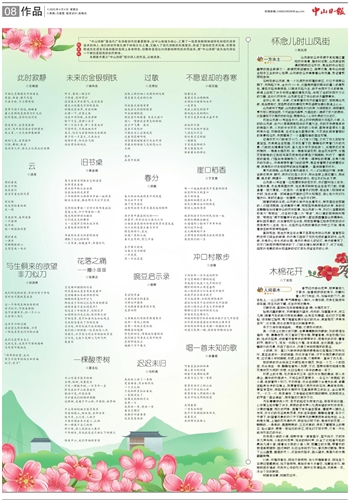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