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第一次到家里的院子,是十年前的一个早晨。那时它瘦得像片影子,肋骨在皮毛下清晰可数,是我在街边的垃圾桶旁捡回来的,仅一个巴掌大小。
它的毛色是不起眼的土黄,脊背上有一绺深色毛发,像干涸的河床,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巴根。耳朵半耷拉着,左耳尖上有个月牙形的缺口,眼睛是深褐色的,看人时总带着三分警觉。
它来这里已经十年了,要论有意思的事,它卧着的时候最有意思。前爪并拢伸向前方,后腿蜷在身下,尾巴轻轻卷着,恰好围成一个半圆。有时睡熟了,会发出轻微的鼾声,胡须随着呼吸微微颤动。
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爬上东墙,它就开始了一天的巡视。从灶房到院门,从院门到灶房,从灶房到我的房间门口,它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停下来嗅嗅。墙根的野草长了多高,枣树落了几颗青果,柴垛里有没有野猫藏身,都被它一一记录在案。
这些年里,院子里最有趣的是它和麻雀的较量。每年春天,总有一对麻雀在屋檐下筑巢。它便整日守在下面,仰着头,一动不动。麻雀故意在它头顶扑棱翅膀,它也不恼,只是轻轻摇摇尾巴,像是在说:嘿,等着瞧吧!我就在下面等着呢!这场对峙往往要持续到雏鸟离巢。十年了,它从没逮到过一只麻雀,却依然年年守候。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守候些什么,除了我和麻雀。
三年前我得了严重的肺炎,走两步路腿都会发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那些日子,它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外。夜里我咳嗽,它能听出轻重。若是咳得急了,它就用爪子挠门,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鸣。有天深夜我发起高烧,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什么在扯我的被角。原来是它不知怎么顶开了房门,正用嘴轻轻拽着被子,一双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像两盏小灯。那一刻我才觉着,这院子里不只有我一个人在活着。
但,它渐渐老了。去年开始,它的巡视路线短了一截,不再走到最远的西墙角。它的胡须白了,跳跃时后腿会微微打颤。但它依然每天送我到大门口,看我走远;依然在日落时分趴在门槛上,等我归来。
前些天,我发现它开始往院子的各个角落里藏东西:一块磨圆的石头、半截皮绳,甚至是我丢失多年的钢笔。它把这些宝贝分别埋在枣树下、水缸后、柴垛旁。我发现时,刚想训斥它,低头却望着它那一副如同孩童犯错被抓个正着,委屈巴巴的模样,不知说些什么好。
昨夜有秋雨,它破例挤进我的屋里,在床脚找了个位置卧下。雷声滚过时,我能感觉到它在发抖,便伸手轻抚它的头顶。它安静下来,把下巴搁在我的拖鞋上,呼吸渐渐平稳。我们就这么相伴到天明。
今早雨停,它又开始了例行的巡视。步子比年轻时慢了许多,在每处埋藏东西的地方都要停留很久。阳光照在它花白的脊背上,那些斑驳的毛发再也看不出一丝尚且年轻的证据。
望着它老去,我明白,终有一天,这个院子里会只剩下它留下的那些痕迹:墙角的抓痕、门槛上的卧痕、石板上磨得发亮的路径。但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当最后一代麻雀也飞走时,这些根还会在土里默默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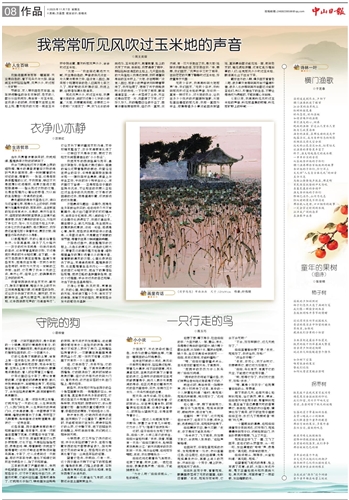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