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农特产,而每个镇街的各个村又有各自的骄傲,并以此成为传统流传下去。
比如沙溪镇的象角村和圣狮村,产出的西洋菜和通心菜堪称一绝;涌边村专门生产菜苗,现在的中心市场一个角落里,就有他们固定的两个位置,卖各种时令菜苗;而水溪村的菜心则在中山市里也广有口碑。
菜心都种在近水的地方,而萝卜需要的水相对来说要少点,就离水源远点,所以,我们对菜心好一点,对萝卜差一点。从六岁开始,爷爷就叫匠人箍了一对小木桶给我挑水用,我爸是长子,我是嫡孙,爷爷的意思是我用不上了还有弟弟妹妹可以用。
我快乐的儿童生活就从六岁开始了,又可以说是农民的辛苦劳作开始了。每天跟着爷爷屁股后面去地里玩,种菜,除杂草,挑水淋菜。很早就体会到当农民的乐趣与辛劳。种菜心我父亲是把好手,种的菜心横平竖直,一起种一起收,相差不了两天,这个本事连爷爷也望尘莫及。
种萝卜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萝卜的根开始膨大之前很省事的,从泡种子到出苗到它的根长成之前,都需要非常少的水分,而到它的根开始膨大了,就需要大量的水。而地离水沟又太远,我还记得弯弯曲曲地走十一个弯,爬六个或缓或陡的坡才能把水挑到地里,中间还要避开别人地里的木薯等作物,不然一不小心就把水桶绊了,白给别人浇水,这是挺懊恼的事。而最让我们揪心的是有一年雨少,溪水断断续续地断流了,而山塘又不敢放水以免影响第二年的春耕,以致我们一下课就疯了似的往溪边跑去跟别人抢水。那是寒冬腊月,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但我们的心都是热乎乎的。那一年的萝卜似乎比往年的更大一些,更白一些。
卖菜永远是一件辛苦事,可是在我妈眼里永远是小事。
一个村里的老奶奶问她,“你的菜心多少钱一斤呀?”她说,“很便宜的,才三分钱一斤。”老奶奶又说,“我要四斤才能够两顿,一毛钱卖四斤给我好不好?我不跟别人说。”我妈说,“好,卖给你。”语气干脆,好像不费工夫一样。按她的说法是,反正地里有,能换成钱都卖,我们缺的是钱,不缺力气。
我就学不到我妈的洒脱。
从小我就跟妈去卖菜,圈子也渐渐地从沙溪到大涌,从初中开始单干,转移到市里,毕竟萝卜在本地销量有限。一般是我用单车驮一箩筐,三叔拉两箩筐,三叔在市里砖厂卖力气,我卖完了就自己拉三个空箩筐回去。
我家的萝卜好,水分十足,又大又白,又甜又脆,炖肉清炒煮汤都很好,最好的腌制成萝卜干,送粥下饭一流,是我们当时淡季的主菜。
因为品相好,一般上午菜市场收摊前我就卖完了,可是那一天是见了鬼了,顾客老是不来,原来卖一毛钱一斤的上好萝卜,到后来开价八分钱也无人问津,倒是快散墟的时候市场的菜贩子来了,围着我的萝卜看了看,拿起来掂了掂,吊着眼问:“多少钱?”我老老实实地说:“全称了,六分。”好歹人家要一天守在那里,这个钱就是要慢慢熬时间挣来的。“五分卖不卖?我是看你小,拉回去也拉不动,好心给你买了。”菜贩子不知真假地说。我看了看地下的三个箩筐,估计还有一百斤出头的萝卜,是怎样也拉不回去的,守着等下午开墟?称了给他少卖一块多钱,还是多守五个小时,在农村,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了。于是,我打定主意,拒绝了菜贩子。熬到快一点钟,花两毛钱吃了个斋粉。好心的老板在上面加了一勺腩汁,那香味余香缭绕,过了四十多年,还仿佛是昨天的事。
倒霉的事都是连着的,眼看快到五点钟,我又大又白的萝卜才卖了一筐,还剩八九十斤的样子,倒是给挑剔的顾客翻得蔫蔫的,无论我淋多少水上去都一样。那个菜贩子又踱过来了,老远我就看见他了,连忙喊他:“老板,来,萝卜卖给你。”菜贩子不情不愿地走过来问:“舍得卖了?现在想卖多少钱一斤?”我连忙说:“五分,五分称给你。”菜贩子斜着眼睛看了看我:“五分!小兄弟你看看市场上有多少萝卜?三分,最多三分称了。”老实说,就算他给两分钱我也要给他了,我是没办法把它拉回家的。想着亏了的两毛钱,想着肚子又饿了,想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萝卜落到如此的下场,眼底里的泪水都快冒出来了。
今年,老妈身子不良于行,地由我继续种,特意种了大萝卜。今天开始拔萝卜,回家一称,足足三四斤一个,又脆又甜,味道像极了四十多年前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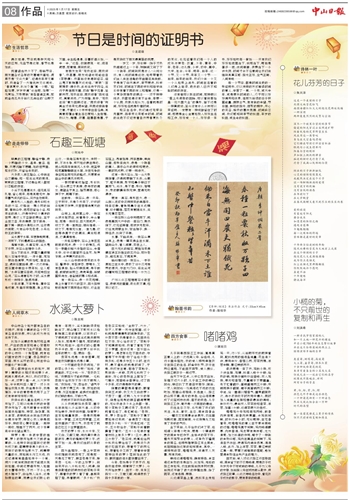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