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那吊脚楼,已四十个春秋。楼顶的炊烟,却如魂灵一般,缠绕着我,在异国的街角,在客地的黄昏,冷不防便从眼底浮出,袅袅地上升。
幼时,炊烟起,便是母亲的手势。她在火塘灶前,屋顶便排出青白的烟来,曲曲折折向上腾升。我自溪边捉螃蟹归来,望见那烟,便知锅中米已熟,腹中的空城计唱得更响了。烟有时浓,有时淡,浓时饭已煮好,淡时火将熄未熄,母亲的脸便在火光中一明一暗。
读书时节,晨起离家,日暮方归。走过三里山路,饿得眼冒金星,忽见远处那缕细烟,便如尝到了饭菜的滋味。烟直则饭熟,烟斜则火微,我竟能从烟的姿态中,辨出家中的动静。味蕾在口中苏醒,脚步也不觉加快。
后来入山背木,百斤重负压肩,汗如雨下。每至力竭,便抬头寻那炊烟。一见烟影,便知家不远,肩上木头也轻了几分。烟是无声的鼓励,是疲惫中的一点希望,支撑着我走完最后一段山路。
从军离家,千里之外。梦中常见那缕炊烟,竟能穿透梦境,引我回家。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不知是汗是泪。烟在梦中不散,家在心中长存。
海上采访,风急浪高,舰如落叶般颠簸。我立于甲板,军舰破浪而行,钢铁巨舰在怒涛中纹丝不移,舰艉的烟柱却如故乡的炊烟般笔直。浪花飞溅间,我紧握湿滑的栏杆,望着那抹坚定的青烟,心中默念:烟在,家在,国在。
为稻粱谋时,常有茫然失措之际。案牍劳形,忽抬头,恍惚中又见那烟。它自我心底升起,穿过岁月,指引方向。烟是魂魄所系,是迷失时的路标。
而今闲居,那炊烟更频频入梦。夜半惊醒,窗外月光如水,恍惚中似见烟影浮动。四十年来,人事几番新,唯有那烟,依旧如故。
炊烟一缕,系我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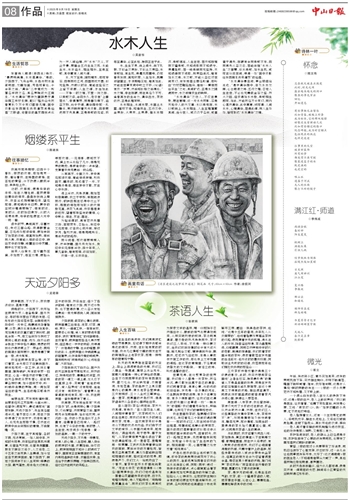
 中山日报微博
中山日报微博
